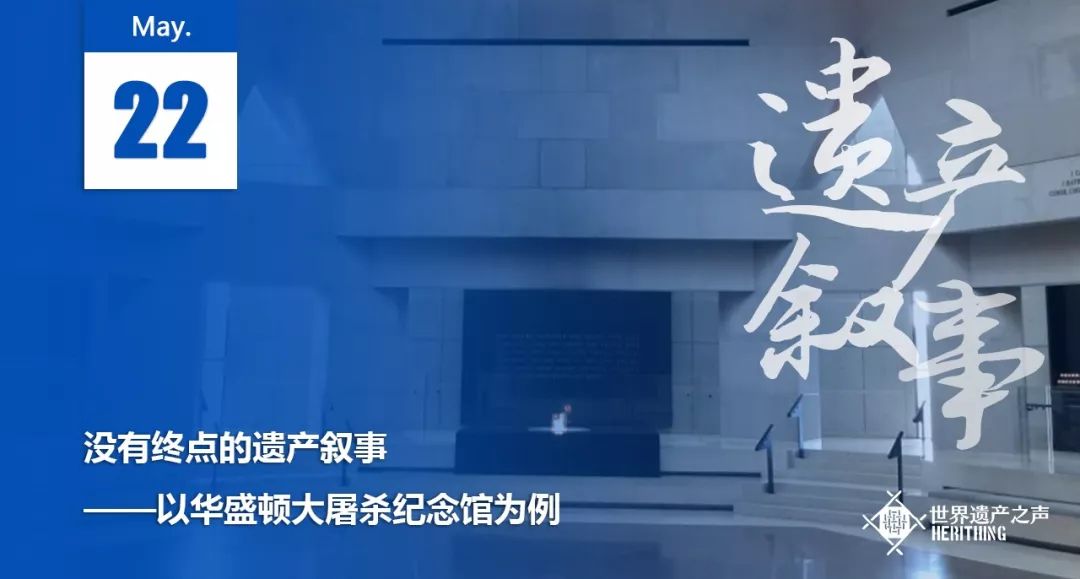
没有终点的遗产叙事 ——以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为例
作者:燕海鸣
绝大部分的文化遗产展示中,都习惯遵循这样一种叙事方式——从最初的梦想开始讲起,直到在某个时刻升华和终结。如果是通史类的展陈,最后的时刻必将是“现在”;如果是某一个遗产,也要终结在某个“终点”。这既是我们所熟悉的展示方法,也是一种相对容易操作的方式。
但是,这样的叙事往往会带来一个问题,即“故事终将结束”。无论是那些伟大的古迹遗址,还是贯穿至今的波澜历史,到了展览的最后,都必须“结束”。这种“从开始到结局”的逻辑,虽然是我们现代人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但并不足以展示历史的五彩斑斓,更不是历史的全部。展览可以告一段落,也可以升华;但是,历史从未终结。
这种叙事逻辑,也和我们今天的生活语境所采用的时间观密切相关。现代社会普遍认为,历史是不断前进的,时间是一种线性的存在——未来必将替代过往,明天注定胜过昨日。在这种线性时间观的指引下,我们普遍相信——明天会更好。
不过,这恐怕只是一种理念,而不是事实,更不应该成为遗产展示阐释的原则。尽管无论政治话语还是生活逻辑,“明天会更好”的语调无所谓对错;但是,对于根本目的是解读和阐发历史记忆的遗产而言,我们必须强调的是——
历史更多时候是循环往复的。
这座纪念馆的展陈设计从最初便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关注和压力,成为争议的焦点。最初的设计方案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是比较典型的演进式的“线性”叙事,即让参观者通过一个有序的时间发展顺序,从大屠杀的初始到结束,去领悟大屠杀。但是,博物馆筹备委员会质疑,这个方案最终指向的是一种“解决”(resolution)。也就是说,当观众离开博物馆时,得到的结论是:大屠杀解决了!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温暖的结局(warm ending)。但是,大屠杀纪念馆的意义显然不是告诉我们大屠杀结束了,而是要让人反思和警醒。因此,这个方案遭到了否决。
经过了几番反复,大屠杀纪念馆最终采用的叙事关注点是“个体”。以个体的故事和个体案例,展示人性中的善与恶。
比如一层的展厅“丹尼尔的故事”。丹尼尔是生活在纳粹时期的一个普通德国男孩,展厅通过模拟当时丹尼尔生活的陈列,塑造了一个拟真的场景,将参观者带回了那个时代。从男孩丹尼尔的视角,该展厅向人们讲述了普通一家人在大难将来之时的迷茫,身处灾难时的恐慌和无助。通过一个孩子的声音,大屠杀展现出它残酷之外的另一面,那就是身处漩涡中心的那种恐怖的安宁。生活似乎仍在继续,但其实生活已经失去了本应有的色彩和味道,丹尼尔的小世界中有着许多的小小甜蜜,但他似乎还没有长大到能够体会到甜蜜背后的苦涩。
另一个曾经的临时展厅,回顾的是当时波兰的一个犹太小镇的生活。德国军队在这里建立了ghetto——犹太隔离区。镇长为了尽量维持小镇的正常生活,不得不周旋在德军和居民中间,尽自己最大可能保护镇民,特别是保护孩子们的基本生活。展厅重现了当时小镇的诡异但又安稳的状态,向人们讲述了人们在扭曲生活中的挣扎。普通人面对巨大的社会动荡根本无从抵抗,但他们却付出了最大的能力来尽量在动荡中保持平常的生活。历史已经证明,镇长以及镇民的勇敢,不比战场上牺牲的烈士逊色。
人性中的善,所反衬的是人类的恶。
地下一层的展厅带我们回到了两千年前的耶稣的年代,讲述了犹太大屠杀的宗教历史根源。少数犹太人杀害了耶稣,但所有的罪恶和仇恨却由整个犹太民族来承担。到了近代,西方社会纷纷建立民族国家,却将犹太人视为排斥的对象。这种仇恨因为一本书的出版而达到极致。《犹太人贤士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是19世纪俄国秘密警察为诬告犹太人“阴谋”统治世界的杜撰文件。该书在西方世界影响巨大,在展厅中,甚至有日文的翻译本,据说日本国内在当时也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而形成了很强的反犹太势力。历史有时候是非理性的。如果说西方主流社会排斥犹太人还有历史宗教等原因的话,那么和犹太人自古毫无瓜葛的一个东方小岛也能产生那样强烈的反犹情绪,的确让人非常触动。
正因为大屠杀的根源是恶,所以它无法通过所谓的“社会发展、时代进步”来自然解决,也注定会面临历史循环的挑战。把历史大叙事回归到个人的故事,也能够让观众有更为深刻的体验,才令观众对乔治·桑塔亚纳那句名言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忘记历史的人,必将重蹈历史的覆辙”。
大屠杀纪念馆的结尾,并没有总结到“大屠杀终结了”。在二楼的走廊上,配有留言簿,与其说是让参观者留言的本子,不如说这些留言簿本身也成为了展出的一部分。从头翻到尾,我们能够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分享他们的心情,读到了人类社会对那段灾难历史的集体反思。看到一段话,是个以色列人写下的:“这不只是我们自己的记忆,这更是整个人类应该记住的过去,感谢大屠杀博物馆,让我们重新体会到当年父母们的辛酸,只可惜,他们已经无法在这里分享这种感动了。”
在这里,历史没有结束,坏的历史没有变得更好。这里所呈现的,只是在历史中时隐时现的善与恶,在记忆里循环往复的美与丑。
遗产的故事没有终点,也不需要终点。因为,人性没有开始,更没有结束。
本文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19年5月21日第5版





